参考文献:本文引用自“医学辅助生殖后 COVID-19 妊娠的孕产妇和新生儿结局(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of pregnancies with COVID-19 after medically assisted reproduction)”,作者是伊冯娜·齐尔特博士:德国汉诺威汉诺威医学院生物统计学研究所;代表作有【医学辅助生殖后 COVID-19 妊娠的孕产妇和新生儿结局:前瞻性 COVID-19 相关产科和新生儿结局研究的结果】;【患者报告的结局评分是否可合理替代手术治疗肩锁关节损伤后的临床随访】;【基于跨学科综合肿瘤学小组的计划对增强癌症患者的复原力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影响:前瞻性纵向单中心研究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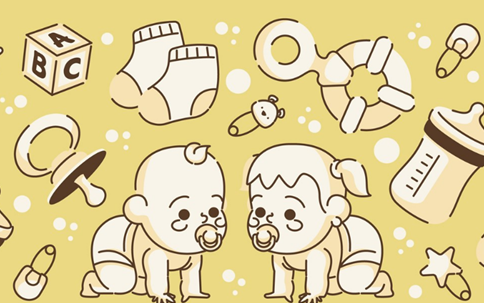
一、介绍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人们担心SARS-CoV-2病毒感染是否会对妊娠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观察性队列研究报告,与未感染者相比,妊娠期感染SARS-CoV-2与严重的孕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新生儿并发症有关。1, 2, 3, 4, 5 来自德国 Covid-19 相关产科和新生儿结局研究 (CRONOS) 登记处的数据前瞻性地招募了在怀孕期间确诊感染 SARS-CoV-2 的妇女,这表明早产和死产的风险更高,并证实重症 COVID-19 的发生率很高,需要对这些妇女进行重症监护。 6,7对于患有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合并症的孕妇和老年妇女尤其如此。8, 9, 10, 11 这些因素也经常出现在寻求生育治疗的女性中。然而,关于风险因素与不孕症治疗的相互作用是否会进一步恶化COVID-19妊娠的结局的数据有限。
在 2020 年 2 月大流行开始时,由于极大的不确定性,生育诊所将治疗推迟了几周到几个月。在引入安全措施和接种疫苗后,中心恢复了常规计划。然而,许多患者仍然不确定,并且非常需要有关SARS-CoV-12感染风险的建议,特别是因为与自然受孕相比,生育治疗后的怀孕已经与产科和新生儿不良结局(如先兆子痫、胎儿生长受限和早产)的发生率显着增加有关。票价:13、14、15 元。为了获得更好的咨询,重要的是要知道COVID-19是否比自然受孕后受孕的女性更频繁地影响接受生育治疗的女性的结局。因此,我们按受孕方式评估了SARS-Cov-2感染中孕产妇和新生儿不良结局的风险,重点是有症状的COVID-19女性。
二、材料和方法
研究设计和设置
CRONOS 是德国围产医学学会 (DGPM) 于 2020 年 2 月建立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旨在快速提供数据,为怀孕期间感染 SARS-CoV-00021208 的女性提供咨询。有关该研究的信息可在德国临床试验注册库获得;部分研究结果最近已发表。7该研究获得了伦理批准(基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学医院,文件编号D 451/20,每个研究方分别分开)。临床确诊感染SARS-CoV-2的妇女有资格纳入。
所有德国妇产医院都被邀请参加CRONOS登记。截至 24 年 2021 月 157 日,来自 115 家德国医院和奥地利林茨开普勒大学医院的产科医生和新生儿科医生确认参加。其中,224家医院积极向CRONOS提供数据。这些产科单位在647年接生了2020,29例分娩,占德国分娩总数的1.2%。参与医院被要求登记所有感染SARS-CoV-<>的妇女,而与怀孕期间的感染时间无关。
三、数据采集和研究变量
为了收集数据,使用服务提供商 castoredc.com(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基于云的电子数据采集平台开发了报告表格。在患者知情同意后,每个治疗医院在数据采集平台中输入有关人口统计学特征、合并症、既往和当前妊娠特征、SARS-CoV-2特异性症状和治疗、妊娠和分娩特定事件以及新生儿结局的信息。7
四、队列
此处提供的数据是在 3 年 2020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15 月 2819 日期间由 10 家医院收集的,共有 8 例病例。在审查登记册和合理性检查期间,有98起案件怀疑有重复条目;其中63例确诊,在与进院人员接触后被排除在外。在2例病例中,感染时的妊娠周仍然未知,并且被排除在外,因为这被认为是强制性信息。在其他650例病例中,尚不清楚妇女是否在怀孕期间或怀孕前被感染;这些也被排除在外。在其余2,1812名怀孕期间确诊感染SARS-CoV-68的妇女中,有3名(709.26%)有症状,8名(129.4%)无症状,9例(19.2%)病例没有提供症状数据(图)。用于分析的最终研究队列由COVID-1485(有症状的SARS-CoV-1331感染)患者组成,他们提供了关于在当前怀孕之前是否进行了医学辅助生殖(MAR)的有效信息(n = 89)。其中,6例(2.30%)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检测到的病毒RNA确诊SARS-CoV-2感染,0例(2.45%)通过检测母体SARS-CoV-3 抗体,0例(75.5%)通过抗原检测,1例(2.<>%)没有关于SARS-CoV-<>感染确切诊断检测的信息。
为了比较MAR后怀孕和自然受孕之间的分类变量,分别列出了每组的绝对频率和相对频率。使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检验对分类基线变量进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并对分类母婴结局应用单变量(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连续变量显示为每个组的均值和标准差。通过使用独立t检验和连续母婴结局的协方差单变量分析,对连续基线变量的统计学意义进行检验。
除P值外,还计算了风险估计值(比值比[OR]或平均差[MD])和相应的95%置信区间(95%Cl)以比较孕产妇和新生儿并发症。为了计算多变量(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中的调整估计量,模型中包括了两组(混杂因素)或已知不良结局危险因素之间显着差异的基线变量。
使用社会科学统计包(SPSS;第28版;IBM Corp, Armonk, NY) for Windows(Microsoft, Redmond, WA)。默认情况下,SPSS 通过删除存在缺失值的个案来执行分析,因此统计分析中的样本数量可能会有所不同。推论统计以描述性的方式使用。因此,既没有确定全局显著性水平,也没有确定局部显著性水平,也没有对多重性进行调整。然而,P值<.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表1420列出了95名(6.65%)自然受孕妇女和4名(38.1%)MAR后怀孕妇女的基线产妇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在所有MAR妊娠中,大多数(n=43;66.2%)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ART)(即体外受精[IVF]或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实现的。9名妇女(n=2.3%)在诱导排卵(OI)后受孕,有(n=3)或没有(n=16)宫内人工授精(IUI),24名妇女(6.<>%)没有进一步指定生育治疗。
总体而言,通过MAR受孕的女性明显年龄较大,并且比自然受孕的女性更有可能未生育或多胎妊娠。两组COVID-19发病时的胎龄相当。
COVID-19相关的孕产妇结局,例如住院治疗需求、肺炎、孕产妇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和孕产妇死亡率,在MAR和自发受孕之间没有差异(表2)。此外,两个受孕组之间与COVID-19相关的剖宫产、终止妊娠或分娩的几率相当。
COVID-4发病后19周内出生后新生儿不良结局主要是由于MAR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入院率显著升高,这也是围产期综合结局临界显著差异(P=.05)的主要原因(表2).这种显着差异主要是由于MAR受孕中多胎妊娠的数量增加,因为当控制多胎妊娠时,受孕模式的调整OR不再显着(补充表3)。虽然在自然受孕后的妊娠中发生了11例死产(2.5%)和1例新生儿死亡(0.2%),但在MAR受孕中没有此类病例的记录。
与COVID-19发病无关的自发受孕后或MAR后分娩的其他孕产妇和围产期结局见补充表1。MAR后的女性更有可能被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比值比[OR],1.97;95%置信区间[CI],1.00-3.86),宫颈功能不全(OR,4.65;95%CI,1.72-12.56),并且更有可能接受剖宫产(OR,2.19;95%CI,1.26-3.82)。然而,多胎妊娠的剖宫产率在受孕组之间相当(OR,0.88;95%CI,0.16-4.71)。围产期出血更常发生在MAR妊娠中(OR,3.33;95%CI,1.35-8.21)。此外,妊娠相关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率较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2.39;95%CI,0.99-5.75; P=.053)。MAR受孕的儿童早产(OR,2.98;95%CI,1.66-5.33)和入住NICU(OR,2.28;95%CI,1.25-4.16)的频率高于自发受孕的出生。虽然罕见,但新生儿死亡在MAR妊娠中的比例更高(1/57=1.8% vs 3/1,145=0.3%)。在任何病例中,新生儿死亡与COVID-19在临床上都没有联系。
选定孕产妇和新生儿结局的多变量(名义)逻辑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在补充表2和表3中。为了估计MAR与自然受孕的调整OR,两组之间在基线时显著差异的母体年龄、未产和多胎妊娠等变量作为协变量被纳入。因为 BMI >30 kg/m 的女性2在MAR组中比例更常见,肥胖是不良结局的已知危险因素,BMI >30也被考虑在内。然而,它在研究样本中没有统计学意义。妊娠相关高血压疾病显示出临界显著差异。因此,还针对这一重要结果计算了多变量模型。
在 COVID-19 的背景下,多变量模型表明,MAR 不是妊娠期糖尿病、妊娠相关高血压疾病、剖宫产、宫颈功能不全、围产期出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入院以及 COVID-4 发病后 19 周内新生儿入院、死产和新生儿死亡的综合围产期结局的统计学显著预测指标。然而,MAR 组的风险仍然更高(OR >1)。MAR显著增加了早产的风险(OR,2.32;95%CI,1.19-4.53),然而,多胎妊娠是早产的主要危险因素(OR,15.92;95%CI,6.82-37.16)。
所有其他多变量分析表明,MAR以外的危险因素是不良结局的主要驱动因素。妊娠期糖尿病与 BMI >30 相关(OR,3.25;95% CI,2.25-4.70);妊娠相关高血压疾病与 BMI >30(OR,2.37;95% CI,1.36-4.13)和未产(OR,2.74;95% CI,1.57-4.77)有关;剖宫产与产妇年龄(OR,1.04;95% CI,1.01-1.06)、BMI >30(OR,1.80;95% CI,1.34-2.43)和未产(OR,1.46;95% CI,1.12-1.91)有关;宫颈功能不全与多胎妊娠有关(OR,14.46;95% CI,5.35–39.09);围产期出血与产妇年龄(OR,1.07;95% CI,1.00-1.13)和多胎妊娠(OR,3.47;95% CI,1.11-10.86)有关;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NICU) 的入院与母亲年龄(OR,1.07;95% CI,1.03-1.10)和多胎妊娠(OR,11.38;95% CI,5.10-25.37)有关;最后,围产期合并结局与多胎妊娠相关(OR,6.14;95% CI,1.90-19.91)。
五、主要发现
我们报告说,在MAR妊娠妇女中,COVID-19相关不良结局的风险,例如,需要住院治疗、肺炎、氧气通气、孕产妇死亡和分娩,以及COVID-4发病后19周内出生后的死产和新生儿死亡,与自然受孕后的妊娠相当。MAR也不是受COVID-19影响的孕妇中孕产妇或新生儿不良结局的主要危险因素。相反,其他因素,如产妇年龄、未产、BMI >30 或多胎妊娠是关键驱动因素。然而,MAR 受孕与妊娠期糖尿病、围产期出血、宫颈功能不全、剖宫产、早产和入住 NICU 的风险较高有关。
六、已知上下文中的结果
几项队列研究报告称,与未诊断为 COVID-19 的孕妇相比,妊娠期 COVID-19 与孕产妇和新生儿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增加之间存在关联。10这涉及先兆子痫,3,16,17妊娠高血压,18孕产妇死亡,19死胎19早产,17,20以及胎儿生长不良等。18,21有合并症(如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的女性的风险显著更高;老年人的风险也更高。8, 9, 10, 11
关于通过MAR和COVID-19实现的怀孕结果的见解很少。第一批数据由ESHRE COVID-19工作组提供。它收集了来自80个国家的32例病例,包括67例活产、10例流产、2例死产和1例孕产妇死亡。22报告病例中有三分之一为无症状感染,31.4%在医院接受治疗。作者的结论是,MAR后妊娠感染不会比自发受孕后导致更高的不良结局风险。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结果一致,该结果表明受孕模式不是受COVID-19影响妇女不良产科和新生儿并发症的主要危险因素。特别令人鼓舞的是,与COVID-19直接相关的患者(如肺炎、ICU住院和死亡)的并发症发生率相当。
Engels Calvo等人报告说,在试管婴儿后有症状和无症状的SARS-CoV-2感染妇女队列中,先兆子痫和剖宫产的发生率高于自然怀孕。23这与我们对这两种结果的观察形成鲜明对比。分析的一个主要区别是重要混杂因素的调整,其中包括西班牙研究中的母亲年龄和临床表现。23在该队列中,36名女性中有74名受孕于供体卵母细胞,这不是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协变量,而是先兆子痫的几个已知危险因素之一。24, 25, 26 此外,IVF患者的剖宫产率高于自然受孕,这尤其可以通过西班牙研究中多胞胎率的增加来解释。我们的多名义logistic回归模型包括临床特征(如年龄、未产和多胎妊娠),这些特征在MAR妊娠和自然受孕之间以及已知的潜在混杂因素(如BMI >30)之间有显著差异。开发的模型表明,如果考虑其他风险因素,MAR妊娠的(仍然)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的风险将进一步降低。在我们的自发受孕队列中,大量死产(2.5%)发生在COVID-4发病后19周内,高于德国约0.4%的预期死产率,需要进一步关注。MAR组没有这些病例,这可能是一方面因为登记怀孕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更好地监测和更早分娩这些高危妊娠本身。
与自发受孕相比,不良孕产妇和新生儿结局在MAR后受孕中更为常见,与妊娠期COVID-19的发病无关。27,28不良结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IVF中多胎妊娠的风险较高。29随着该领域向单胚胎移植的方向发展,并且随着多胎妊娠率的降低,其他因素也变得很明显,例如,在冷冻解冻胚胎移植周期30,31,32或低 生育力中选择编程方案33本身对不良结局的发生率较高做出了重大贡献。低生育力妇女更常携带妊娠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例如,年龄较大,肥胖或代谢改变。12,34,35除了预期的更高多胎妊娠率外,我们还在不孕队列中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该队列年龄较大,更经常肥胖。未产率,这是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危险因素,36也更高。我们的多变量模型结果表明,MAR本身并不是受COVID-19影响的妊娠不良结局的主要危险因素,例如妊娠糖尿病、围产期出血、宫颈功能不全、剖宫产、早产和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但这些妇女以更高的基线风险进入妊娠期。在这种情况下,孕产妇年龄、多胎妊娠和BMI>30是产科和新生儿并发症的主要预测因素。
七、临床意义
我们的研究结果在迄今为止未知的持续大流行中具有临床重要性。他们将帮助为寻求生育治疗的夫妇提供建议,并将保证,当患者受到COVID-19的影响时,生育治疗本身不会增加孕产妇和新生儿不良结果的潜在风险。然而,我们的数据再次清楚地表明,其他可能可以避免的危险因素(例如,多胎妊娠)会导致较差的结局。
八、优势和局限性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利用了使用标准化电子临床报告表进行监督良好的前瞻性注册研究。纳入了专门针对MAR的项目,并与COVID-19以及产科和新生儿结局相关联。我们研究的一个特别优势是区分受孕方法,如IVF或ICSI和OI,有或没有IUI,这确保了数据输入的质量。由于无症状病例很可能被认为是“偶然SARS-CoV-2感染”病例,由于其他原因需要住院治疗,因此我们将分析重点放在有症状的女性身上。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方法避免了主要因为产科并发症(如自发性早产、胎儿生长受限或先兆子痫)而就诊的女性。
我们的研究存在多种局限性,包括MAR妊娠的样本量相对较小,因此队列规模不同。这些因素使得难以可靠地显示统计相关性。然而,我们的队列反映了德国的现实情况,大约4%的新生儿是通过MAR进行的。由于队列设计作为注册研究,因此无法得出关于两个受孕组中受 COVID-19 影响的女性并发症的实际发生率的结论。7同样,由于目前病例数较低,无法就严重产妇病程和新生儿感染的危险因素作出最后陈述。此外,无法与没有COVID-19的女性进行比较,因此无法得出对结果的直接影响(COVID-19与无SARS-CoV-2感染)。
九、结论和今后的方向
MAR 后妊娠期间的 COVID-19 与 COVID-19 相关不良结局的风险显著增加无关。然而,与自然受孕后的结局相比,孕产妇和新生儿发病率增加。这些数据为寻求生育治疗的夫妇提供咨询提供了重要信息,并保证与怀孕期间 COVID-19 的自发受孕相比,风险主要不是由 MAR 驱动的,而是其他个人风险因素。随着全球SARS-CoV-2感染数量的增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我们的观察结果,并阐明不同的SARS-CoV-2变体以及先前免疫接种后的感染对产科和新生儿结局的影响。
HSG方便、廉价,可以检查输卵管近端和远端的阻塞,显示峡部的结节性输卵管炎,了解输卵管的细节并评估输卵管周围的炎症情况。
IVF实验室的胚胎学家在取卵前应与临床医生核对患者信息,在临床医师对患者实施取卵术时,应该同步进行捡卵操作。
PGD过程中的胚胎活检是一种创伤性显微操作,有可能影响活检后胚胎发育能力。在进行胚胎活检之前需要在透明带上打孔或者部…
胚胎冷冻保存对FET妊娠率以及子代出生缺陷率没有显著影响。在液氮中细胞的酶活力几乎完全被抑制,细胞代谢过程处于停滞状…
胚胎冷冻保存技术是辅助生殖技术(ART)重要的衍生技术之一,是指将胚胎置于超低温环境(液氮,-196℃)中冷冻保存,…